纪实文学与小说的界线并非如我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泾渭分明,它们本就是一母同胞的兄弟。或许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这样的:归类为小说时,作者强调的是其文学技法,而从何取材这一问题是退居二线,甚至无关紧要的;归类为纪实文学时,作者强调的是故事绝不容忽视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一切的前提。
1
同为大屠杀题材,娜塔莎·沃丁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常常与塞巴尔德的《奥斯特利茨》拿来相提并论。二者的地基一个是虚构,一个是现实,但拔地而起后它们指向的是同样的内核:追回被淹没与被遗忘的逝者。同样是笼罩于寻亲的谜团云层之下,塞巴尔德选择了极度风格化的绝对虚构,但与之对照的是他在小说中安插了大量注释般的代表着绝对真实的照片,现实与虚构形成了迷幻的交织缠绕;娜塔莎·沃丁则选择了纪实的书写方式,但这个故事魔幻得像是不真实的发生,甚至有时会让读者有一种这是小说的错觉。但它的题材归类为纪实文学,这个分类像一个喇叭或一根刺,当我们从心理上妄图逃避书中的悲惨世界时,它提醒我们:这就是荒谬而残忍的现实。
 (资料图)
(资料图)
书中在描写战乱时有着完全超乎于常规认知的情节:一个钢琴家生下了缺了六根手指的孩子,没有别的粮食只吃南瓜的人全身都变成了橙色,生了病的孩子突然发疯般地想吃巧克力,这样的情节令人很容易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例如同样描写黑暗家族史的《百年孤独》。魔幻现实主义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挂靠现实,比如经典的“飞升”桥段,其飞升媒介是常见的床单。某种意义上,《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可被称之为现实魔幻主义——现实已经魔幻得近似于超现实,但我们头上始终悬挂着“纪实文学”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个无时无刻鸣笛的沉重提醒。
整本书被分割成了四部分,四个部分各自独立却又彼此应和,被统御于一个使命之下——让逝者重生,让逝去的历史重生。四个部分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视角,第一部分是身为作家的追亲者的索隐探秘,第二部分转述姨妈莉迪娅尘封的回忆录,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都是讲述母亲叶芙根尼娅的故事。沃丁以自己的出生时间为切割线,所以在第三部分她的笔触接近于一个历史考据学家,而第四部分则在大量时间里透过在当时还身为孩子的作者的眼睛去观察。书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片段,正是源自这种孩子头脑的想法和成人世界的绝望两者的碰撞。混杂着的不同的语调音符组成了紊流般的时代交响曲——大革命、大饥荒、大清洗、劳改营以及之后对夹杂在政治与历史中“永恒的难民”的种种迫害,演奏出那些消逝却又永存不散,清晰却又迷雾重重的血色乐章。
整本书所带给我们的荒诞感和残酷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差异:愿景在历史进程下的不堪一击(祖母玛蒂尔达相信眼下的一切只是一阵喧闹,随时会烟消云散);理想在现实情况下的事与愿违(为革命而奋战的外祖父在革命后被流放并且失去了自己的女儿);战争的侵蚀和政治的迫害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的反转(姨夫尤里患有肺结核,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不幸最终让他避免去前线,救了全家的命)和颠覆(“恰恰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多么珍贵,多么令人喜悦”)。
2
最令读者感到压抑的是作者对于婚姻困境的勾勒。对于女性们来说,战时,结婚与爱无关,只是为了生存,为了一点可能平时微不足道的许可和权力。在《暗影中的人》里,这种处境被浓缩总结成一句话:“人们结婚,生子,离婚又再婚,仅仅是因为艰难的日常生活难以独自应对。”战后,婚姻则变成了地狱,沃丁以一种在讲述常识道理的口吻写道:“如果她在乌克兰,她可以抛下父亲逃走,和他离婚,但是在德国,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任由父亲摆布。”
作家作为一个游移在过往时间黑洞中的探秘者,同时占据了两种视角,一方面作为后来人,她有着超越当时历史环境的全知视角;另一方面,作为追寻者,她依然无可避免地有着局限视角。即使是拥有了第一手的关于人物的资料(例如姨妈亲手写的回忆录)亦无法完全看清那些反光的疑团。第二部分里经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话:“这并不是她回忆录中的唯一盲点。”“这句话旁边并没有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又留下一个盲点。”更不用说全书随处可见的一连串的对往事的想象猜测,这些疑问从初始一直蔓延到末尾:“为什么她最后还是没有带上妹妹和我,为什么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离去?”
于是,我们拥有了一种奇特的体验:作者向我们提供了足够多的记录与事件,同时又向我们抛掷出了无数巨大的永不可解的谜团。这种永不可解显示了一种追探历史真相导致的必然的失落,正如普里莫莱维——另一位伟大的书写集中营的作家所说的:“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被吞没者,才是彻底的见证人,但他们已经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于是母亲才会常把“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挂在嘴边,而作为女儿的作者也希望见到母亲曾见到过的,哪怕一次就好。这是无法跨越的天堑鸿沟,而展示这种永恒的距离本身就足以产生无尽的颤动。
3
《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从头至尾沃丁几乎没有失控,黑暗的内核始终被包裹在技法的蚕丝里。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跟随着作者的步伐一点点拨开家族历史的朦胧面纱。第一部分的叙事带给了我们一种近乎侦探小说般的感受,同时我们也享受着身为文学作家的叙事者优美雅致的文辞。而在第二部分,由于姨妈也是文学专业出身,某种程度上一些文学性的描绘——譬如“每当巨大的鲟鱼群和梭鲈鱼游过时,平静的海面犹如沸腾一般”——究竟源自于作者还是姨妈的笔触这一问题成为了模糊混淆的光晕。直至第三部分,文学性描绘的海水渐退,浮现出坚硬质地的传统非虚构写作常用的引述与引用方法,来自于各个机构中的文献,来自于当年世代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话语,当然还有一些来自于并不清晰的回忆。
在第三部分里最为惊悚的则是在这种抽离姿态的语境中插入的两段关于当下时空的情节:作家在租房子时出现了一个对她心怀不轨骚扰她却从未付诸强暴行为的醉鬼,他常使用本地方言称呼她为“俄国女”,直到她回溯过去时才明白这个词来自于德国劳改营时期;德国医生为作家诊断虹膜时发现她的虹膜有许多结构缺陷而不敢置信、认知坍塌。这种根植于他们内心的想法追根溯源是当年德国的洗脑——“有些生物结实,因为他们劣等”。
历史的铁丝依然勒紧着被迫害者们的躯体,这是曾经创痛的伤痕从未愈合的铁证。或许更令我们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故事依然在发生着,历史的水银又一次轮回到了原来的刻度。
关键词: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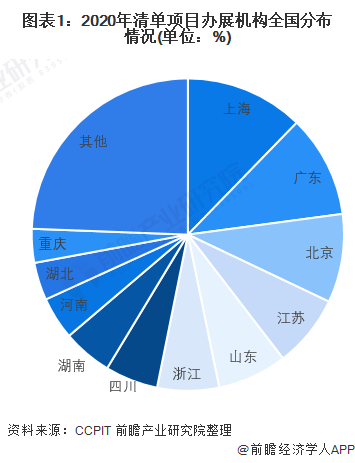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